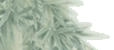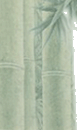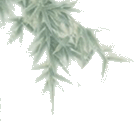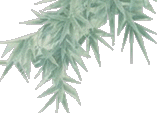|
水西庄原址位于清时天津城西五里南运河的南岸,雍正元年由查日乾、查为仁父子开始修建。最初占地“广可百亩”,后经几次扩建,面积达
150亩之多。
天津地处渤海之滨,为九河下梢之地,自古以来就有舟楫、鱼盐之利。清朝初年,为充裕国税,政府鼓励豪绅富户经营盐业。在康熙年间先后将长芦盐政署、长芦盐运司从北京、沧州移至天津,从此天津便成为了清代盐商的大本营,这极大地刺激了天津的快速发展。
以盐业为龙头的经济发展和盐商的崛起,从而导致了盐商文化的诞生。这与当时天津撤军事建制卫,改行政建制州,又升州为府,发展为京畿地区一大封建都会也是相辅相成的。因为,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,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上层建筑。据周汝昌先生考证,时,查日乾助大盐商张霖为业,获得京师食盐的专卖权,年收入十万至二十万两白银,遂成巨富,来往于京津两地,俱有产业,水西庄诞生,实源于此。
据史料记载,查日乾、查为仁父子虽是商海巨富,但有祖上读书、“好儒”传统,可谓一代儒商,具有很高的文学修养。他们在经商之余,喜结名流雅士,与之诗文唱和。
水西庄的修建,是盐商经济在文化上的反映,也是当时政治需要的产物。水西庄的诞生,促进了这种文化的交流和发展。在天津,与水西庄同期兴建的还有其他一些私家园林,但规模和品位均不及水西庄。查为仁在《抱瓮集·水西庄诗并序》中是这样记载水西庄兴建过程的:
“天津城西有地一区,广可百亩,三面环抱大河,南距孔道半里许,其间榆槐柽柳之蔚郁。暇时,侍家大人过此,乐其水树之胜,因购为小园。垒石为山,疏土为池,斧白木以为屋,周遭缭以短垣。因地布置,不加丹垩。有堂有亭,有楼有台,有桥有舟,其间花袅竹,延荣接姿,历春绵冬,颇宜觞咏。营建既成,以在卫河之西也,名曰水西庄。”
又据《天津县志·水西庄记》载:
“既成,亭台映发,池沼萦抱,竹木荫庇于檐阿,花卉纷披于阶砌。其高可以眺,其卑可以憩也。津门之胜,于是乎毕揽于几矣。”
由此可见,水西庄“面向卫水,背枕郊野”,凭河造景,巧夺天工,是一处交通方便又十分清幽雅致的园林。园中楼台亭榭有名可考者计 34 处,如揽翠轩、藕香榭、数帆台、枕溪廊、泊月舫、花影庵、秀野、红板桥、一犁春雨、碧海浮螺亭、来蝶亭、苔花馆、香雨楼、竹间楼等。这些楼台亭榭的起名,每个都是依据其特点,富有诗情画意,清新雅致,丝毫没有商贾的那种俗气,折射出浓郁的文人高雅文化氛围。游人登临这些景点,听其名,观其景,势必会触景生情,“颇宜觞咏”。
例如数帆台,高耸于运河之畔,登台远眺,势必会出现“长河一望征帆远”、“轻帆挂去小楼空”或“几程风雨奈何天,片帆西望碧云边”的情景。
“长河落日,白帆悠悠”的绝妙景观,直到 20 世纪60年代天津犹可见到,只是后来各河断流、干涸,津门才失却了这道美丽古朴、宁静致远的风景线!天津多坑塘湖泊湿地,历来为鱼、米、藕之乡。
莲藕栽培,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,天津四郊还比比皆是。天津50岁以上的人都会记得,20世纪60年代以前,卖肉是以鲜绿的荷叶作包装的,何况清时!风清、荷绿、藕香,藕香榭,正是当时风韵的真实写照:身处秀野,会使人幻发“惹烟笼月影檀案”,“无数秋光上修竹”的浮想……就水西庄的整体构思与布局而言,体现出了高超的造园艺术水平和深刻的文化内涵,为当时津门一绝,这是无可质疑的。然而,如此规模、如此造诣的园林艺术,与其他方面比起来,不过是“小节”(红学家周汝昌语,后有全文介绍)一桩,可见水西庄文化的博大精深!此其一。
第二,的确,水西庄蕴含的文化底蕴是我们今天三言两语难以述说的。例如,水西庄的收藏相当丰富。这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它对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视、发掘与继承,为开天津高雅文化之先河做出了巨大贡献。以查礼为例。
查礼( 1715 - 1782 )自幼聪慧颖悟,平生酷爱文物。因购得一绝妙古代铜鼓,遂名其书房为“铜鼓书堂”。他集秦汉铜印六百余方,其中“官印自王侯将相至蛮夷番属,应有尽有。私印自朱文小印至篆虫鸟之文,无不具备。”后来,他按时代之顺序,排列成谱,编纂成《铜鼓书堂藏印》一书。
其子查淳,继承父业,又集历代铜印“三百有奇”,总共千余方。仅此一项就蔚为大观,至今无可匹敌。庄内藏书,据查淳自述:“累数万卷”珍品字画有《双凤图》、《松阴高士图》、《载鹤图》、《湘漓江源图》、《对床风雨读书图》、《荆树再花图》、《枯木竹石图》、《长江万里图》、明杨文宪墨迹、清吴天章字等法帖类有《旧拓兰亭禊贴》、宋黄庭坚书《蓄狸说》拓本、宋黄庭坚、苏轼书《东坡赠李方叔》拓本等。
第三,水西庄建成后,促进了南北文人的交往,对天津文化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清代着名文学家袁枚在其《随园诗话》中记说:时,升平日久,海内殷富,商人士大夫慕古人之风,蓄积书史,广开坛坫。扬州有马氏秋玉之玲珑山馆,天津有查氏心谷之水西庄……名流宴咏,殆无虚日。
水西庄的优越地理位置、优雅的环境,加之水西庄主的“喜交游”,讲义气,“重然诺”,豪情待客,一掷千金,致使“贤豪长者多乐归之”,南来北往的文人雅士常在水西庄小憩甚至常住。他们与主人“赠答唱酬”、鉴书赏画,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诗作、书画珍品和趣闻逸事。据史料记载,与水西庄交往甚密的名流先后有诗人陈元龙、津门海光寺名僧元弘、画家恽寿平、著名文学家袁枚、诗人徐兰、画家朱岷、胡峻、陈元复、《四库全书》的总纂官----“一代文宗”纪晓岚,还有文人墨客马祖荣、钱载、杭世骏、吴廷华、汪沆、厉鹗、刘文、万光泰、陈世倌、赵昱、金玉冈等等。这些当时顶尖的文人,留下的诗作、书画作品难以计数,不少为珍品佳作。
如乾隆二年朱岷在水西庄揽翠轩所画《秋庄夜雨读书图》,上有汪沆、刘文、吴廷华、葛正等名家题识,一展水西庄雨景,成为研究水西庄的重要资料。
特别是水西庄第二代主人的着作《莲坡诗话》,既是一部优美的散文和笔记小说作品,又是一部纪实之作,有很强的史料价值,是研究水西庄和天津历史、文化,追寻清代众多着名文人墨客踪迹的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。
查为仁与钱塘厉鹗共同撰着的《绝妙好词笺》于1750年出版,后被收入《四库全书》,至今仍被视为词文学研究的必读文献。
此外,研究天津的重要典籍----天津自有地方行政建制以来的最早志书----乾隆年间版的《天津府志》、《天津县志》皆修自水西庄。
第四,皇帝多次驻跸水西庄。据史料记载,自1748年起,乾隆皇帝曾十次来天津,其中四次驻跸水西庄。皇帝多次巡幸天津驻跸水西庄,其原因固然与水西庄的的舟楫便利、环境幽雅、饮食丰美有关,但更重要是出于经济和政治上的考虑。
乾隆皇帝为一代明君,深知水西庄的巨大影响和其主人所代表的社会力量之重要。他要改变先帝对盐商富豪的压抑、限制,以“怀柔”政策亲近他们,主动与之对话,消除以往隔阂,让他们在政治上心无疑虑地依附皇权,在经济上心甘情愿拿出巨资以充国库。他四次驻跸水西庄,就是这种姿态的展现。乾隆皇帝成功了----他的四次驻跸不仅取得了盐商阶层的信任,还紧紧抓住他们办了多件实事。
例如,乾隆三十六年(1771年)二月,乾隆皇帝第二次驻跸水西庄时,在芥园主持论证了一项水利工程,并召见赏赐了长芦盐商,还对上年水灾灾民进行了赈抚。乾隆三十八年(1773年)三月,乾隆皇帝第三次驻跸水西庄,主要目的是“阅视河工”,即视察运河的水利工程,同时下旨缓征长芦盐商银两,等等。
这一切正如大红学家周汝昌先生所一言以敝之:“水西庄的事关系着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建设、文艺创作等等众多方面的大事----最后才是园林艺术的‘小节’”。限于篇幅,本文所述挂一漏万,但水西庄在天津历史上的地位,读者还是能够管中窥豹略见一斑的。
子牙河畔将重现名园丰姿
水西庄的兴衰,实际上是国运的反映。大清国康乾盛世,水西庄崛起兴旺;大清国日渐衰微,水西庄则失去活性;大清国消亡,则水西庄荡然无存。
然而,对于曾兴盛百年,又废屺百年的历史名园,津门人士一直没有忘却,复活它的梦想久存。清末民国初,有盐商黄铁珊出面,筹款备料,以图复建。因时国运不济,复建计划落空;20世纪三十年代,正值中国动荡之际,有严智怡等一批热心文人出来组织水西庄遗址保护委员会,打算寻踪重建,然依时机不当,致奔走呼号再付东流。
改革开放,国逢盛世,身为津沽之子的大红学家周汝昌先生,首倡成立水西庄研究学会,以期为名园的重生而奠基。此倡议得到了红桥区委、区政府的大力支持,“水西庄学会”遂告成立。
红桥区委、区政府的领导认识到,水西庄对于红桥,对于天津的意义,绝非仅是一座私家园林,它的出现,代表了天津历史上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。
研究水西庄文化,梦想复建水西庄,不仅是对古代优秀文化遗产的挖掘和继承,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填补天津旅游资源的缺乏,完善天津的城市功能,从而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,带动红桥和天津的发展。基于此,红桥区委、区政府的历届主要领导同
志亲自兼任水西庄学会的理事长。
“水西庄学会”的成立,使京津两地乃至全国及海外百余名有关专家、学者、作家、查氏后代聚集其下。经过大家刻苦工作、潜心研究,十年时间,成果颇丰,为水西庄的复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周汝昌先生曾在《团结报》等各种报刊上发表文章,多次呼吁海内外查氏后人能行动起来,为重建中华名园水西庄而贡献力量。
文章引起金庸先生对水西庄的关注。1996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,金庸先生与周老谈及此事,表现了查氏后人对津门水西庄的极大热情。
水西庄的此次复建,址选子牙河畔平津战役纪念馆侧。因原址已有众多建筑,不宜拆毁。目前,水西庄复建的初步方案已确定,并得到了市有关部门的批准。名称为水西庄公园。拟复建原水西庄的30余个景点,如揽翠轩、数帆台、藕香榭、泊月舫、淡宜书屋、竹间楼、古芸室、香雨楼、来蝶亭、秋白斋等等。此外,还要建立一些功能区,使之成为集文化娱乐于一体的大型公园。
目前正加紧设计,争取明年破土动工。津门儿女盼望水西庄的再度崛起!
|